17位北漂家政女工,公开展示被家暴、劳作中的身体(组图)
今年春天,
一群家政女工登上舞台,
跳了场酣畅淋漓,又极先锋的舞蹈。
舞美别具风格,
从全国各地征集500件红色衣物,
包括衣服、围巾、毯子、丝袜,
象征月经和血液,
也隐喻冲破世俗对底层劳动女性的成见。



▲
身体剧场呈现后现代的舞蹈形式“接触即兴”
下图摄影:李润筠
6月底,
一条跟拍两位参演身体剧场的家政大姐,
从北京东辛店人均200的出租屋,
到高档酒店员工宿舍,
她们从城市各角落出发,
前往望京一间45m²的地下室,
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家政姐妹相聚。

▲
北京东辛店住家阿姨牛会玲的出租屋
这个故事讲述时代流动下的家园,
也关乎一个人,如何寻回她的尊严。
撰文:陈沁


▲
《分·身》演出剧照(摄影:李润筠)
内蒙人梅若记得,第一次密集接触家政工群体,还是十几年前。她去拍纪录片,对象是40个家政女工。
跟拍的过程里,DV机就架在真实的生活场域。夜晚无人入眠,镜头前,忽然凑上来一个“大头”,对着机器倾诉感受:“现在是晚上11点,我刚搞完卫生,回到房间里”,梅若被那种真实感撼动了。
在此之前,她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。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,后来到北京念大学,她学法律,爱好广泛,却一直热心公益。

▲
鸿雁办公室的家政工影像照片墙
拍家政工纪录片那年,她已经结婚,有了孩子。她感到进入婚姻家庭后,女性想要获得成长,阻力无处不在。即便自己获得的社会资源,已经不算稀薄,但“还是如此难”。
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,平移到这个边缘群体,意识到她们的处境更难想象。据统计,北京家政工从业人员,超过60万。在整个中国,数据则是3700万。其中,超过95%是女性。
这个庞大的底层劳动女性群体,生活在城市,却像隐形的存在。她们面临的问题,还没有在公共讨论的语境中被真正地重视过。
随着老龄化、二胎开放,城市家庭照料的市场需求剧增。梅若笃信,在很长的周期里,家政工这个议题,都不会消失。

▲
摄影:丁沁
公益行业也有“赛道”。梅若花了很长时间,向别人论述,为何家政女工是弱势群体?她把这个称为“破题”。
不像罕见病患者、流浪儿童和残障人士,家政女工的权益不是紧迫的议题。在人们看来,尤其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,家政女工收入不菲,“照顾老人有5000,照顾孩子有7000、8000,月嫂甚至要上万”,梅若说。
但当一个女性,多数是从乡村、县城来到大城市,孤身一人,抑或举家前往,再然后,原子化地进入到一个城市家庭里头,她们的处境是复杂的。无论是主动,还是被动成为一名家政女工,背后的命运都稍显沉重。

▲
家政大姐们在《分·身》登台演出前(摄影:李润筠)
很少有人在这份职业里,体会到价值和尊严。而在一份可观的收入背后,大多数人背负的经济压力,平常人很难想象。很多女性,是在突然遭遇家庭变故后,决定到城市里来。譬如,丈夫过世,父母生病。又或者,到了某个用钱的关口,孩子上学或结婚,赚来这些钱,大部分要寄回老家去,很少属于她们自己。

▲
《分·身》排练中的李文丽(摄影:李润筠)
梅若记得最极致的一个故事。这里面,是一个流动女性普遍的隐忍和自我剥削。
“一位住家阿姨,一个月几乎不花钱,最多花到100块,而周末即使休息一天都会有愧疚感,她觉得出来就是挣钱的,怎么可以去享受?”
还有好些是被家暴出逃,到了城市,再也不要回去。2011年拍摄纪录片时,梅若认识了一个东北大姐,丈夫酒后,把她的胳膊打断三节,尾椎骨也被打断。因为丈夫一喝醉酒就打她,后来她索性到北京街头流浪,做了家政工。
另一些,则是在养育孩子的周期,出来照料雇主的孩子。于是,城市远方的另一个孩子,不得不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。
当然,还有这个群体始终在面临的不确定性,“今天在这家做,明天会不会下户,那明天住在哪里?”

2014年,梅若开始做家政女工的调研。两年后,她和一个朋友,成立公益组织“鸿雁社工服务中心”,她们租借一个空间,又把望京的一个地下室,变成主要的活动中心。
在内蒙,有一首歌叫《鸿雁》。鸿雁靠迁徙越冬,聚集成数十、数百、甚至上千只的大群。“就像这些家政女工,要通过迁徙来赚取她们的生计。”
前前后后,“鸿雁”聚集过三四千个家政工。一开始,这里像一个“诉苦”大本营,“因为大家都挺苦的”。也解决一些功能性的问题,比如,教初来城市的女性,如何使用手机导航,寻找就近免费的公园,以及一些法律援助。再往后,她们做绿色家政,也做家政女工艺术节。


▲
演出现场有近200名观众
上图摄影:丁沁 下图摄影:李润筠
4月初,在一个真正的剧场,17位家政女工登上舞台,演出身体剧场作品《分·身》,这也促成了我们这次的拍摄。我们好奇的是,一个极具艺术感的舞台背后的生命故事。
在镜头前,当她们讲起前半生,常提到“压抑”。过去,那些苦闷与愁情,像溶洞底下翻涌的大河,心在翻转,但无人知。而孤雁找到雁群,便有暂时栖息之地。
她们也形容自己是“地丁花”,开在石缝,路边,荒野,春天。


6月底,北京接近40度。周六这天,家政工通常休息。
五环外,崔各庄东辛店的早晨,沿街低矮商铺与密集出租房里,生活快要苏醒了。这里与望京CBD仅一墙之隔,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
我们见到牛会玲,她50岁出头,山西临汾人,始终笑意盈盈。她带我们穿过狭长巷弄,来到她租住的6m²的“家”。租金600块,她和两个姐妹合租下来,人均只要200块。


▲
牛会玲在6m²的出租屋
平日相聚的机会很少,她是住家阿姨,只有周六才会过来,可以睡到自然醒,打扮打扮,吃个早饭,就坐公交前往望京。
这个家仅容纳一张床,还有一些换季衣物。床沿到门口的距离,几近只有一步。但她在这里,有她的快意。她喜欢那扇小窗,通风,光能照进来。
高中毕业后,她就开始做乡镇小学老师,教语文和数学,一直持续27年。早些年,学校是寄宿制,她吃了好多年食堂,其实不太会做饭。但她热爱和孩子相处,把很多爱都给了学生。

在北京做住家阿姨后,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弱点,人生过了一半,重新开始学习厨艺。家政工是她的第二份工作,我们问她是否感到职业落差,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从来没有低人一等。
但来北京的第二份工作,是在一栋别墅里,工资开到8000块,常被雇主“呼来唤去”,别墅有三层,一顿饭她要端着盘子上下跑三次,两个月后她请辞,她要留住她的自尊。
变故,是发生在丈夫生病那一年。丈夫病了几年,每年都进抢救室,加上孩子结婚,家里早已入不敷出,欠下不少外债。她决定出来打工,用她的话来说,“把这个家撑起来”。
很快,丈夫去世。人生最低谷的时候,她感到生命快要死去。北京城大得像一个荒野,她险些无法从中走出来。“鸿雁”托住了她的一些痛苦,所以只要休息,她总往那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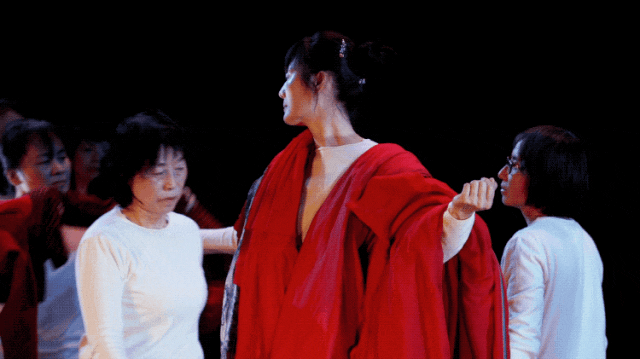
▲
故事情节根据家政工姐妹被家暴经历改编
上图摄影:丁沁
她提到在身体剧场《分·身》里的一个故事,当家政工李文丽把自己的身体化身为一个衣架时,“我们所有人把衣服搭在她身上,一起说,‘你没有家了,你能去哪儿’?”
每当排练到这儿,她都泣不成声,看到她哭,所有的姐妹都产生共鸣。漂泊在外,牛会玲自视为“无家可归的人”。哭完,她们停下来互相拥抱,互相安慰,情绪平复后,再接着演。
在望京45m²地下室里排练的这几年,被迫停下的时刻总有发生,大家停下来抹掉眼泪,因为很多情节,完全来自真实的生命经验。


甚至,把打鸡蛋、系围裙、颠锅、洗衣服,也搬上舞台。宋廷会惊讶于这样的表演,“自己当演员来表演自己的事儿”,这简直是头一遭儿,“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展现,我们永远都是最边缘化的。”
宋廷会是重庆人,远嫁到河北涿州,上午在一个酒店里做面点师,下午她做小时工,固定给一对小夫妻做晚饭。
她把自己的打工生活切割成两块,穿上白色的厨师服,她有稳定的营生,工资有两三千块,住在有电梯、空调的宿舍,拥有保险。而脱下厨师服,她成为一个家政小时工,补贴一点家用。

▲
宋廷会下班后
周末休息日,如果不去“鸿雁”,她就回到在南六环马驹桥的出租屋,给家人做做饭。她是最早一批加入“鸿雁”的家政女工。七年间,她加入不少文艺小组,参加过三届艺术节,写下她从日常生活里得来的诗句。
而在《分·身》里,她最喜欢的是谭启容和罗雪芳的一段双人舞。当她们相拥,并不得不告别的时刻,“我要走了”,这句台词总让宋廷会产生撕心裂肺的感受。

▲
在舞台上,呈现哄雇主孩子入睡时唱《小星星》的片段
她想起自己出来打工时,儿子才6岁。她一次次和父母、孩子告别,她认为这是一种“无奈地出走”。还有一段,是在舞台上,大家唱起《小星星》。她想起小时候陪孩子,几乎没给他们唱过什么歌,如今唱起歌来,却是在雇主家哄雇主的孩子入睡。
家政女工的生活,似乎始终在面对一种分裂。大时代底下的流动女性,从乡村来到城市,从一个家庭来到另一个家庭,身体的劳动带来生计,却也带来身体与情感的分离。
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
一个长在城市 霓虹闪闪车灯亮
一个生在家乡 星星点灯蛐蛐唱
……
啊 啊 我像一只鸿雁
飞越了南方北方 漂泊在人海茫茫


▲
《分·身》排练现场
《分·身》的排练极尽周折。
虽然跨越三年之久,但排练其实只有36个周六,在第37个周六正式登台演出。这期间,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又回来。
过去十年,身体工作者廖书艺,一直在和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打交道。作为《分·身》的导演,她形容这次身体剧场的排练,“是在传统的剧场排练中,无法想象的工作节奏。”

▲
导演廖书艺和家政大姐们排练中
很多家政女工是流动的,最少的时候,只有三个人能来。这个过程里,罗雪芳始终坚持到场,即便往返排练,她要坐50站公交,花去至少5个小时。雇主家和排练室两点一线,可疫情起伏的那一年,她也常常提心吊胆。
疫情和家政的工作属性,带来太多不确定性。廖书艺觉得,整个创排过程就像“缝被子”。不能贪多,因为一周只能见一次,需要“一小点一小点慢慢积累下来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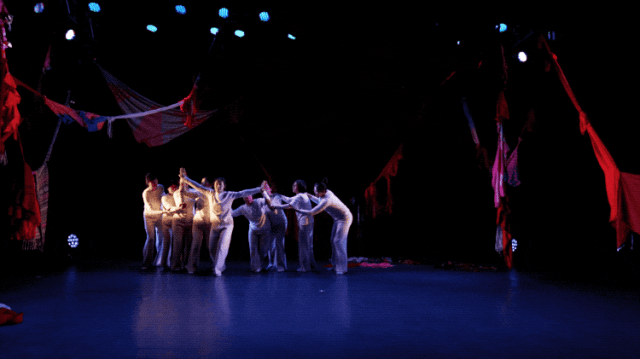

▲
摄影:丁沁
“接触即兴”,作为后现代舞蹈的一种,强调在动态中感知身体间的对话,探索动作中的“共享时刻”,主张人人皆可舞。
一开始,好多大姐不认为这是一种舞蹈。比如宋廷会觉得,舞蹈总归是在电视上看到的,像民族舞、现代舞,她脑海里都有鲜明的画面。而在地板上翻滚,身体纠缠在一起,就像退回到孩童时代,这怎么能算是跳舞?
但廖书艺发现,这些家政大姐的身体质感非常好,很“接地”。过去她和白领一起跳舞,感知到她们身体的疏离,“因为长时间坐着,跟地板不太亲密”,这是家政大姐带给她的惊喜。

▲
摄影:丁沁
这样的惊喜还有,当谭启容和罗雪芳在双人舞中,像磁石一样相拥在一起,廖书艺发觉自己根本不用告诉她们,应当用什么节奏来演绎,因为那些情感总是“准确”的。
她教给她们一些最简单的动作,让她们去觉察身体。抬起手臂,再放下,如此反复,她们由此联想到颠锅时的经验——她们有自己对于动作的理解。慢慢地,这部作品里,形成了许多看起来是“写实”的部分。

比如系上围裙,再抖动,如同即将开始劳作。而解下红色围裙之后,将之化作毛笔,身体变成洗衣机、彩绸、风扇……总之,像极了将劳动场景搬上舞台。虽然构设这部作品时,并没有如此严格的对应。
廖书艺认为,“这个作品好像真的把她们的生活卷进去了,有点分不清楚到底是在表演,还是在生活。”

▲
摄影:李润筠
4月8日,北京天桥剧场,灯光暗去,在鸟鸣声中,家政女工陆续走上舞台。在牛会玲的记忆中,演出前一周的最后一次排练,大家仍旧会哭得“稀里哗啦”,情感太浓烈了,她们担忧是否能完整演完。
作为五幕剧,每一幕的内容,想要讨论的主题不一,但都关乎身体。当家政女工的身体,被城市生活切分,她们作为女性、劳工、妻子、母亲,身份时刻变换。
开篇故事,来自家政女工高冬梅的经历。2015年,她从山西到了北京,刚上户,在雇主家的客厅里,雇主和她说话,她没有回应,而是愣在原地。她的普通话不好,过去在家乡,唯一能听到普通话的机会,是在电视机里——她以为是电视机在说话,这是普通话第一次闯入她的空间。
语言差异背后,也是身份的鸿沟。身体就这样被分为几个:生理的,工作的,家乡的……

在被家政工们叫做“拉重物”的一幕,红色衣服道具,变成了各种象征。在舞台上,她们想象自己如何拖拽生活的重量前行。她们逐个高喊,让这些重量化作:一袋大米,一桶油,50斤面粉,一袋白菜,一袋土豆,50斤猪肉,一箱苹果,一车砖头,一家人。
拉不动怎么办呢?那就分做好几趟。“第一趟、第二趟”,一位家政女工忽然高声唱起歌来。然后,她们提起这重量,再放下,再提起,再放下,一遍一遍重复,直到最后,狠狠把这重量抛出去。

好多人都在“抛”的过程中感到快意,因为真实的生活里,只能驮负、拖拽、隐忍。
这是宋廷会觉得最痛快的章节,廖书艺告诉她,“可以用不同的节奏、方式去拿起、放下这些‘重物’,轻或重,看看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。”
宋廷会想象,“第一次抛出去的时候,要轻轻地,就像一个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,父母就是这样呵护我们,生怕我们受一点点伤害。但是人生会碰见不同的事情,有时我们也要狠狠地抛回去。”


▲
时隔3个月,家政工们一起观看舞台表演
谢幕时分,17位家政女工,被响亮地念出名字。
舞台具备魔力,它指示了超出生活的一种可能,此刻不委身于厨房,灶台,抹布,消毒剂,照料孩子,护理老人。身体也是值得骄傲的,虽然它必须时刻为生活忙碌,但劳动者的身体光辉,同样属于舞台。
时隔几个月,在望京的地下室里,我们和一群家政女工,一起观看了记录整场舞台的视频。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,仍旧会为一些片段心情激越,感受持久余味。

▲
第一届“百手撑家”家政工艺术节影像作品
梅若想用艺术去唤醒一些东西,这是她做艺术节的初衷。2017年,家政女工们开始有了第一届“百手撑家”艺术节。顾名思义,生计全靠一双手,却可以支撑家庭。
第一届艺术节以纪实影像为主,覆盖北京、济南、西安、上海、广州,她们邀约了5个摄影师,跟踪拍摄100个家政女工的故事,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集结成一本画册,也在北京798的一个画廊公开展映。

▲
家政工姐妹们用红色衣物叠出的"七手八脚"女性形象,由家政工李文丽绘成图样,张东红用口红写出“分·身”,牛会玲手写文字,最终由舞美设计揭小凤设计成艺术节海报
后来,艺术节的主题,则关于音乐与诗歌。家政女工集体创作了一张专辑《生命相遇》,包含10首原创作品,收录了范雨素写的歌词。
其中一首同名歌曲,也是许多大姐最喜爱的一首,歌词几乎是一人一句合力写成。宋廷会写了开头,她说:“整个人生就是稀里糊涂的,稀里糊涂中也有快乐”,还有她最满意的最后一句,“人生如水,终在大海汇聚”。

▲
走出“鸿雁”地下室,需要经过一道暗而窄的楼梯
梅若记得,那年在录制现场,一个叫王青春的家政女工。她性格温柔,却始终唱不上去高音。梅若是做社会工作的,想探究青春失去高音的过程。
于是发现,青春原来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从小她不爱讲话,看见人都只有笑容,没有笑声,是“家里头最不被看见的老二”。
从事家政工作后,她尽力在雇主家“隐身”,日常不太需要说话,只是默默做事,每天最常说的话是“好的”。
梅若唏嘘,或许很多人在经历了一生之后,竟不觉得自己有过“高音”。越底层的女性,从出生那一天开始,就被认定人生应该如何度过。
在某种意义上,“鸿雁”在做的事情,是帮她们找回“高音”。舞蹈,唱歌,写作……年轻时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,忽然接续上了。最重要的是,可以袒露自己。

梅若是80后,她觉得自己和这些家政大姐,其实是同龄人。在家政市场,40到50岁,是最值价的年纪,因为体力最好。50岁往上,住家阿姨的工作已经不太好找。60岁的人在做什么?——在做环卫工,保洁。
流动时代底下,一个城市给人营生,也应当托举她们。很多家政大姐提到“家园”。
牛会玲不再觉得自己是漂泊没家的人,每次见到姐妹们,她都要用力地拥抱。她喜欢朗诵,《分·身》的制作人颜维旭就送她一本女诗人的诗集,她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作品。忙碌的时候,她会一口气念十几首,攒着慢慢发表。

宋廷会觉得“鸿雁”像是一个精神寄托,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家庭。这几年,她也在这里学习环保理念,健康饮食和垃圾分类。而过去,休息的时候,她无处可去,只能游荡在商场和公园。她也写诗,虽然有些羞涩于发表。
诗句就来自生活,一天,她发现员工宿舍床位上的三束光线:
我的墙上有三处光
透过床斜上角的三处光线
照在白的墙壁上
小的是黑的第一束光
中间的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
右边最宽是人生最亮,美好的生活
光亮不仅照亮自己
还要用光去照亮别人
部分素材提供: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







 +61
+61 +86
+86 +886
+886 +852
+852 +853
+853 +64
+64


